作者:春姑娘 2025-07-26
当毛孩子化作星光
你也可以好好哭一场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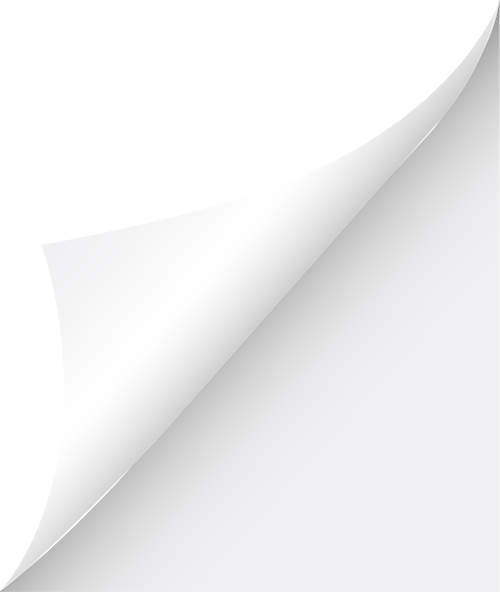
引言
本文章转载自临床与咨询心理实验室的《宠物哀伤 | 当毛孩子化作星光,你也可以好好哭一场》。

“也许在别人看来只是一只猫或者一只狗,但在我心里,那是我的家人啊。”
听到这句话,我心里一阵发酸。因为我知道,这种不被理解的哀伤,对很多养宠物的人来说,是再真实不过的存在。
在过去几十年间,宠物从“看家护院”逐渐成为我们的情感依恋对象。特别是在独居青年、空巢家庭、“不婚不育”人群日益增长的当下,它们的角色不仅仅是陪伴,而是家庭的一部分,是“毛孩子”,甚至是我们人生某段时期唯一的情感支撑。
一份中国宠物行业消费报告显示,截至2024年,犬猫总数超过1.2亿只,90后、00后已经成为养宠主力。与此同步增长的,还有一种被悄悄忽略的情绪:宠物哀伤。
很多人在宠物离世后会陷入强烈的哀伤、自责、甚至生理症状(如失眠、食欲减退)。心理学研究表明,宠物哀伤的主观痛苦程度,与失去亲人高度相似。尤其是当宠物被视为家庭成员时,悲痛、内疚、孤独,几乎是一体而来的。
然而,真正让哀伤变得更难熬的,往往不是哀伤本身,而是这种哀伤“不被理解”。
——“再养一只不就好了?”
——“你又不是没经历过离别。”
——“这不是人,是动物啊。”
这些看似安慰的言语,其实是对你情感的轻视。心理学家称之为“被剥夺的哀伤”(disenfranchised grief):这是一种因为缺乏社会承认、文化仪式或外界支持而被压抑的哀伤体验。
研究表明,这类哀伤比人们想象的更加持久、难以调适,甚至可能演变为复杂性哀伤(complicated grief)或创伤后应激障碍(PTSD)(Adrian et al., 2009)。

很多人以为,哀伤会按阶段线性推进,从否认、愤怒到接受。但实际上,哀伤更像一种动态波动,而不是“完成式的情绪工作”。
面对宠物的离世,哀伤并不会像计划表那样按时结束,它更像天气——今天出太阳,明天又下雨,没有谁能完全掌控它的节奏。我们参考心理学中一个非常贴切的模型——“双程模型”,它告诉我们:哀伤不需要“走出来”,而是会在“失落”与“重建”之间来回摆动。
正是这种波动,让宠物哀伤有了被理解的可能。
这个模型指出,哀伤其实是在两种状态之间不断交替:
丧失导向(Loss-Oriented):
你允许自己哀伤,反复想念、哭泣、触景伤情;
恢复导向(Restoration-Oriented):
你努力回到生活轨道,做饭、上班、约朋友,试着重新适应。
这种“情绪-现实”的交替过程,正是哀伤自然的心理调节机制。不是你反复无常,而是你正在努力复原。
这一模型尤其适用于宠物哀伤——因为宠物的离世,既是情感依恋的破裂,也常常打乱了我们原有的生活节奏。毛孩子们也许曾是你早晨的闹钟,是你回家路上最期待的目光,甚至是你情绪最糟时唯一的陪伴。

宠物哀伤并不只是“缩小版的丧亲之痛”,它有自己独特之处:
(1)单向依恋的断裂更容易引发自责
人与宠物的关系往往是单向的——宠物完全依赖我们,而我们把它们视作孩子、伙伴、依靠。当这种依恋突然中断时,人更容易陷入“我没保护好它”的内疚与失控感,尤其在经历突发意外或无法告别时更明显。
(2)缺乏仪式和情绪表达的合法性
亲人去世有追悼、悼词、亲友安慰,但宠物的离去却常常无声无息。缺乏社会支持与表达空间,会让哀伤变得更孤独、更隐蔽、更难愈合。
(3)对许多人来说,这是第一次面对“死亡”
宠物可能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爱过、也第一次真正失去的生命个体。这种失去往往影响深远,尤其是在儿童、独居者、长者身上格外强烈,可能改变他们对死亡与依恋的理解方式。
(4)它打破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节奏
宠物不仅是情感对象,它们参与了我们的生活结构:吃饭时间、作息、回家后的迎接……它的缺席往往不是一点悲伤,而是整个生活的失衡。
(5)它常常被文化和代际忽视
在很多文化中,宠物还未被普遍视为“家庭成员”,宠物哀伤缺乏明确的社会承认。“你怎么这么夸张”“不就是条狗吗”这类反应会加重情绪压抑与自我怀疑。
以下是一些来自研究支持的调适方式,也许能帮助你走得更轻一些:
(1)允许自己哀伤
你可以哭、可以想念、可以怀疑人生,也可以什么都不做。研究表明,压抑哀伤反而更可能引发长期情绪困扰(Wrobel & Dye, 2003)。
(2) 建立纪念仪式
为它写封信、画张像、点一盏灯,或者在朋友圈发一条怀念贴文。这些象征行为是我们与逝者建立“持续性情感联系”(continuing bonds)的一种方式,可以带来情绪缓冲的作用。
(3)寻求真正能理解你的人
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宠物哀伤。选择愿意倾听的人,比倾诉本身更重要。有时候,仅仅是有人说:“我懂”,就足以让你不再那么孤独。
(4)不急着“替代”
很多人在宠物刚离开时就开始考虑“再养一只”。但研究发现,若个体尚未完成哀伤过程,过快投入新依恋关系,可能加重内疚,甚至影响与新宠物的联结(Messam & Hart, 2019)。
(5)若需要,请接受专业支持
如果你持续半年以上仍无法摆脱哀伤,或已影响睡眠、饮食、人际关系,那可能已属于“复杂性哀伤”或“功能性损害”范畴。心理咨询师、哀伤小组或宠物悼念服务,都是你可以尝试的方式。

宠物虽已化作星光,但爱与记忆永不消失,宠物的离世不是故事的终结,而是你与它之间另一种形式的继续。它们教会我们爱、依恋、责任,也教会我们面对死亡和分离。即使你现在很难过,也请相信——这份哀伤的深度,其实正是你爱得有多深的明证。
愿你在哀伤中被理解、被允许
也终将被温柔地安放!
参考文献:
Adrian, J. A., Deliramich, A. N., & Frueh, B. C. (2009). Complicated grief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humans' response to the death of pets/animals. Bulletin of the Menninger Clinic, 73(3), 176-187. https://doi.org/10.1521/bumc.2009.73.3.176
Cordaro, M. (2012). Pet loss and disenfranchised grief: Implications for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practice.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, 34(4), 283-294. https://doi.org/10.17744/mehc.34.4.41q0248450t98072
Doka, K. J. (1989). Disenfranchised grief: Recognizing hidden sorrow. Lexington Books.
Packman, W., Field, N. P., Carmack, B. J., & Ronen, R. (2011). Continuing bonds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in pet loss. 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, 16(4), 341-357. https://doi.org/10.1080/15325024.2011.572046
Stroebe, M., & Schut, H. (1999). The dual process model of coping with bereavement: Rationale and description. Death Studies, 23(3), 197–224. https://doi.org/10.1080/074811899201046
Wrobel, T. A., & Dye, A. L. (2003). Grieving pet death: Normative, gender, and attachment issues. Omega-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, 47(4), 385-393. https://doi.org/10.2190/QYV5-LLJ1-T043-U0F9
Zilcha-Mano, S., Mikulincer, M., & Shaver, P. R. (2011). Pet in the therapy room: An attachment perspective on Animal-Assisted Therapy. Attachment & Human Development, 13(6), 541-561. https://doi.org/10.1080/14616734.2011.608987
END
编辑:小盐
审校:Kitty
来源:春风心理应激干预